华侨大学教授陈庆妃对话马来西亚华人作家黎紫书——书写华埠:一场漫长的磨合
【作家简介】
黎紫书,1971年生于马来西亚,自1995年以来屡屡获得马来西亚花踪文学奖、台湾联合报与时报等各项文学奖,曾获马来西亚优秀青年作家奖、云里风年度优秀作家奖等,2016年获南洋华文文学奖。长篇小说《告别的年代》获得第四届红楼梦长篇小说奖评审奖。已出版长篇小说《流俗地》《告别的年代》,短篇小说集《野菩萨》《山瘟》《天国之门》,微型小说集《余生》及散文集《暂停键》等。
【作者简介】
陈庆妃,福建松溪人,文学博士,华侨大学文学院、海外华人文学暨台港文学研究中心教授,“海外华人文学理论与批评”方向硕士生导师,中国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会理事,泉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监事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华侨华人文学、香港文学。
马来西亚华人作家黎紫书。(受访者供图/《中国新闻》报 发)【《中国新闻》报作者陈庆妃报道】马来西亚旅台学者陈大为将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三分天下:作为中心的西马文坛、东马婆罗洲写作、马华旅(在)台文学。然而,作为“七字辈”马来西亚华人女作家,黎紫书却是一个很难归类的存在。她的游离,她的荣誉加身与诸方批评共存,理解“这一个”黎紫书,成为本期访谈的初衷。
女性书写(或以“伪男性”方式)几乎贯穿了您所有的创作,从早期的短篇小说集《天国之门》到唯二长篇小说——《告别的年代》《流俗地》。许维贤2001年曾对《天国之门》有所批评,认为您乐衷于演绎“女人神话”。许的批评是建立在对您作为“独树一帜的一流作家”的要求之上的。二十年以后,这还是一个有效的问题。请问这个神话还在吗,或者是换一种方式存在?
黎紫书:我不晓得何为“女人神话”,也不明白一个女作家以女性视角写作,或多以女性为书写对象,这何以值得批评。男性作家写男人(或英雄)的多了去,并不见得会招来一种“乐衷于演绎男人神话”的说法。
2001年,我在写作路上才出道五年,也才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当时说我“乐衷”于什么,肯定言之过早了。那以后二十年我算是笔耕不辍,别人──无论是普通读者抑或是评论家──给我套个什么名头或对我有什么样的要求和期许,我实在是管不上的。但到这时候了,我仍然不明白,把“女性书写”甚至“伪男性方式”(两者根本上是不同的吧?)套在一个女作家头上,有什么意义呢?但凡看见这些性別标签,我总会问:同理能反过来用在男作家身上吗?显然,我从没听过“男性书写”(更別说“伪女性”)这回事。
“独树一帜”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以为对一个作家来说,认识到自己的独特性,写只有自己能写的作品,基本上就可以独树一帜了。当然,“一流作家”是另一回事,那得有眼光,有功底,有创意,有格局。现阶段,我就写我能写和我想写的,这态度和信念赋予我自由,而这种自由既超脱于评论,也超脱于性別。尽管过去二十五年写得不多,但无论写的是微型小说抑或长篇,我的态度都是一丝不苟的,现在也是时候撕掉贴在我身上的各种标签了吧?
陈庆妃:马来西亚华埠锡都怡保是您的众多小说的原发性场景,一个没落的华人小镇,已经不再是开埠时期充满淋漓的野性、属于男性的时代。父亲去哪里了?在“失父”的国度重建生活需要女性柔韧的生命力,面向凡俗、琐碎,承受生命之轻。就您个人而言,是如何理解华族在马来西亚的命运,如何理解华文写作在马来西亚的意义?与不少马华男性作家的抵抗、悲情写作有何不同?
黎紫书:当今之世,每当一个女作家使用“父亲”这个词,便总是带点女性主义的味道,仿佛我们正在委婉地谈论着父权和女性命运这种“终极”课题。我其实并不认同把女性课题都简单地放在父权社会的框架里观看和讨论,我觉得这种视角太狭隘了,最终会造成集体的偏颇。
我个人从不讳言成长经验中父亲的缺席,但我不以为这可以直接拿来裁定我的“女性命运”,毕竟我若是个男孩,家中有个功能崩坏的父亲(或母亲),也肯定会影响我的人生,从而表现在我的写作上。
我的家乡怡保无疑是个没落的华人城镇,但这不意味它就不再属于“男性的时代”了。男性没有这么容易放弃一个时代,时代也不会这样就对一个地方放手。相反的,在一个不够“先进”的地方,人们对性别的观念和态度多半会必较保守些,女性也可能会相对更温顺一些,或者对男性更顺从一些(而这并不表示她们就没有“柔韧的生命力”)。
我觉得自己在本质上没有太强烈的“反抗精神”,至少它不是那么形于色,总要高举拳头大声疾呼。我也不以为华族在马来西亚面对的是持久的斗争,我认为这是一场漫长的磨合。我这么说,感觉就不那么“悲情”也不那么波澜壮阔了,而是有点无奈,却又不失坚毅。
无论是抵抗抑或是磨合,你要我说华文写作在马来西亚的意义,我先想到的是那是我们的骄傲──主要是在别的华族同胞面前自我感觉良好──放到世界地图上,它最能表现马华这群体的独特性,也最能说明我们在文化上的价值观。
陈庆妃:马华作家都有写一本“大书”(有影响力的长篇)的自我期许,以回应自身在华语文学世界的“边缘”位置。《告别的年代》出版后获得嘉誉,您已经告别了“写大书”的焦虑,那么十年后再写《流俗地》有何特别的意义?对您而言,《流俗地》是一本“大书”吗?如果说《告别的年代》中的杜丽安属于“大女主”,《流俗地》中瞎女古银霞无疑是“小女子”,从马华女性代际承续的生命史到日常的生活流、浮世绘,您如何看待家族史书写与日常言说,二者之间孰轻孰重?
黎紫书:《告别的年代》今年要重新出版了。对我而言,当初动笔写长篇也许出于“写大书的焦虑”,因而虽明知有点勉强,仍硬着头皮坚持它写完。无论它得到什么嘉誉,我很清楚这作品完成度不足,达不到我自己的预期。尽管理想中的“大书”并没有写出来,但诚如你所言,那以后我真没有了写大书的急迫感。
十年后书写《流俗地》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之前那“勉力为之”的书写经验对我何其宝贵。《流俗地》看似反璞归真,不少人把它看为朴实的写实主义作品,若是用现代主义的眼光判断,这似乎就意味着作品的创意不足、格局不大。可是它在我心里是真正的野心之作,写一部如此“不寻常”的马华文学作品,比写《告别的年代》需要更大的勇气和自信,而这些勇气和自信,实际上有一大部分就来自之前写长篇的经验。我在刚交上去的新版《告别的年代》序文中,把这部小说比作一道“木人巷”,它是我为以后的长篇作品所做的准备。没有它,我不会写出后来的《流俗地》。
就我本人而言,家族史书写与日常言说无所谓孰轻之孰重的问题,杜丽安与银霞两个女子面对命运和家国,摆出来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姿态,但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骨子里却是一样。我无意抑此扬彼,也无意把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加诸小说人物的身上,让他们成为我的工具。我只在意自己有没有充分展现出我对这些人物的观察和情感。
陈庆妃:您的小说在中国内地“登陆”——发表和出版应该算是很不错。“黎紫书研究”在华人学术圈也算是“显学”,从美国华人学者王德威到马华旅台学者黄锦树、张锦忠,马华学者林春美、许文荣、许维贤,以及内地学者都不吝笔墨,然而“拒绝阐释”却是您的基本态度。您的很多小说一定程度上对此前的学者批评做了抵抗性回应,甚至在小说中设置了学者的批评空间,与之对话、诘问、反驳。学者批评反向驱动了您的创作,可以这么理解吗?
黎紫书:不,你不可以这么理解。这不是一道数学题,不能套一个这么非此则彼的公式。我确实对评论浑不在意;对于我读过的那些学院派的文学评论,多数时候我都觉得有生搬硬套之嫌,不敢苟同。至于那些批评我的作品的,他们评得对不对、有没有道理、是不是有洞察力和创见,我身为作者,更是了然于心。既然我写出《告别的年代》那样的作品来,我对评论的态度也就摆在那里了,不容我辩驳。
我必须承认在那部作品里,我对文学评论摆出了一种揶揄的、不友善的姿态,今天的我应该不至于再如此冒犯,但那是因为我年纪大了,也自省过,再不喜欢这么沖撞的表达方式。可我事实上仍经常觉得文学批评与文学作品像两个平行世界之物,难得有对得上话的时候;或者说,我以为学院派的训练往往使得文学批评(不得不)成为一种壮观又理直气壮的误读。
坦白说,以一个写作人的立场而言,我始终认为这些批评对创作者无益,也就是我不相信有哪个作家会从中获得写作的养分,但我不否认好的文学评论可能会对读者产生一些启发或某种“导读”的作用。
不管怎样,我对批评的不信任实在不影响我写作的动机和方向。《告別的年代》算是个特殊的例子,那个作品算是对批评的一种挑衅,但这种挑衅本身难道不也是可以被阐释的吗?所以我并不认为这是在“拒绝阐释”。
后来写《流俗地》,我是在完成以后才发现,这作品不具备学院对文学作品所提出的好些既定要求,要是交到学者们的手上,肯定会是一项艰难的挑战──我可不是为了挑战学者而写这小说的。
(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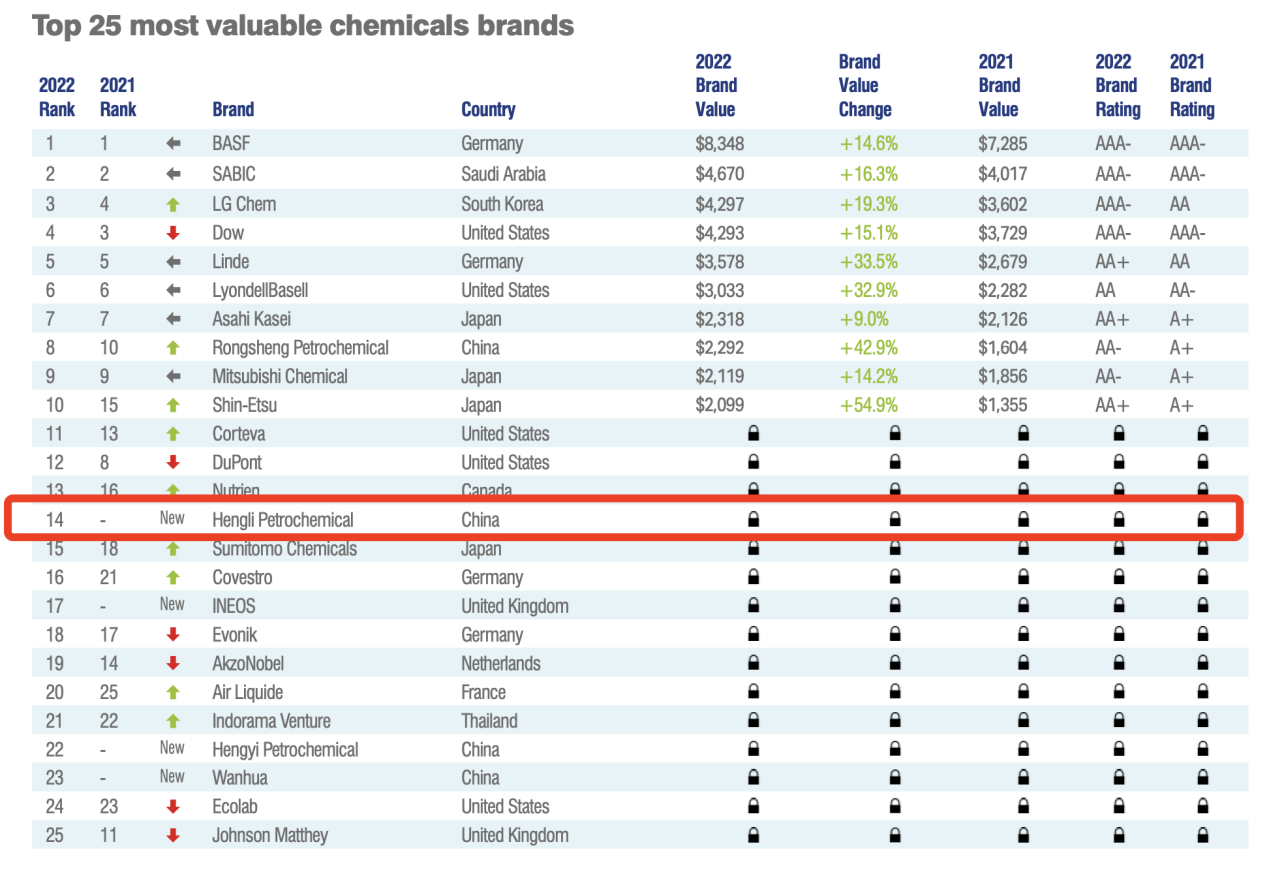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